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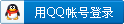
x
(宋·真德秀撰)《四書集編》 《中庸》集編 卷上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兩端之説吕、楊為優。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民,非謂只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輯略:吕氏曰:舜之知所以為大者,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已。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愚、無賢不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邇言者,流俗之諺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合乎衆議者也。邇言出無心者也,雖未盡合乎理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之,出與人同之道也。楊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取諸人以為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為善也。取諸人以為善人必以善告之,與人為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為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之所以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 卷中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逰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故大德者必受命,《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或問十七章之説曰:程子、張子、吕氏之説備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顔、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為顔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説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顔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冥漢之間,尤非所以語顔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為天孔子固己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所以為栽者也,至禄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耳,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説以汨之哉?問舜之大德受命,止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箇物推倒他。理自如此,唯我有是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輯略:程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誤。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氣;德勝其氣,性命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吕氏曰:中庸之行,孝悌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謂盡孝。故禄位名壽之必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一本云:天之萬物,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未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淩雨,則其本先撥。至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禄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歟。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有性焉,不謂命也。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以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禄位名壽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栽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桀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 卷下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内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 天覆地載,萬物並育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徃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或問小德大德之説,曰:以天地言之,則髙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説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内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跡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賛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辨物居方而其廣至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是哉?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川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髙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而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輯略:程子曰:孔子旣知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旣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如俗,言敦本之意。又曰:大德敦化,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合德。張子曰:接物是皆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更須大體上求尋也。吕氏曰:此言仲尼譬天地之大也,其博厚足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冐天下。其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監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並育而不相害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而不相悖之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大德所以敦化也。一本云:祖述者,推本其意;憲章者,循守其法;川流者,如百川派别;敦化者,如天地一氣。又曰:五行之氣紛錯太虛之中,並行而不相悖也,然一物之感無不具有五行之氣,特多寡不常耳。一人之身亦無不具有五行之德,故百理差殊亦並行而不相悖。游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文武,故憲章焉。體元而亨,利物而正,一喜一怒,通四時,夫是之謂律天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五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教修,下襲水土則地理之異宜全矣。故博厚配地無不持載,髙明配天無不覆幬,變通如四時之錯行,照臨如日月之代明,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動者植者皆裕如也,是謂並育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久或速,無可無不可,是謂並行而不相悖。動以利物者智也,故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言川流,則知敦化者仁之體;言敦化,則知川流者智之用。侯氏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所以並育而不相害也;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論語》集編 卷六 《顔淵》第十二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遥;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説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枉與直一例去愛他便不得,大抵為先知了方能愛其所當愛。只此兩句自包上下,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愛人知人是仁智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仁知之體,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問云云曰:尋常説仁智,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别,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裏面有智,智裏面有仁。南軒曰: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智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况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而可以盡仁則不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問知而諭以知人者,亦猶是爾。 卷七 《憲問》第十四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致堂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故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大圭,如奉槃水,如震霆之在上也,淵谷之在下也,師保之在前也,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特敬之道。問:聦明睿知皆由此出,莫是自敬出否?朱子曰: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問程子云云,曰:敬則自是聦明人之所以,不聦不明者止緣身心惰嫚便昬塞了,敬則虚靜自然通達。因問周子云靜虚則明,明則通,是此意否?曰:意亦相似。又問云云,曰:聦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觀之,此心才不虚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聦,冶容亂色交蔽而不辨何以為明,睿智皆出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由思慮得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虚明,然後物不能惑。南軒曰:修己之道不越乎敬,敬之道盡則所為修己者亦無不盡,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蓋一篤敬則推之家以及天下者,皆其理也,極其至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兆民雖衆,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則修己以敬一語,理無不盡者。 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跡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卷十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歴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歴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歳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絶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 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閲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 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責己薄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鍚予善人。蓋本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絶,謂封黄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