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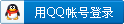
x
潇湘入诗考 陈泳超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1] 潇湘一词诗意醇酽,自不待言。而其积淀之深厚及风韵之绰约,实可算作诗美意象的一例典范。本文将分析潇湘意象的内在情韵及其生成过程。所谓“入诗”者,在本文有两层特殊含义:其一,本文主要以唐诗及唐前文学为考察对象,唐后从略,这是因为潇湘意象的内涵至唐诗始丰满确立,此后并无多大变化,而是作为一种诗美传统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其二,本文虽主要考察诗歌,但亦不自限于诗歌一体,事实上一种意象的美学风格,是会在各种文体中都有表现的,故所谓“入诗”之“诗”,当以诗学自之。谨识于前,以免贻惑读者。 潇湘名称的地理变迁 潇湘今为二水之名。湘江源起于广西灵川县海洋山,辗转北流,于洞庭湖入长江,贯穿湖南全境,故“湘”为湖南省的代称。潇水源于湖南省蓝山县野猪山南麓,曲折北流至永州汇入湘江,是湘江上游最大的一条支流[2]。 但“潇湘”二字的历史却颇有周折。“湘”字作为水名,很早就已单独使用,如《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兕在舜葬东,湘水南。”[3]《楚辞》中“湘”字更常常出现,不必列举。尽管历来对于湘水的源头或流程亦非全无异议,但基本上与今相似,向来没有大的变动。 而“潇”字就全然不同了,在唐朝之前,“潇”字作为水名者,未见一例。最早出现“潇湘”一词而又比较容易引起误解的,是《山海经·中山经》里这段文字: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 依许慎《说文解字》:“潇”字写作“”,释为“深清也,从水,肃声”。这一说法原无异议,但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字注中,却提到了一点别样意见: 谓深而清也。《中山经》曰:“澧沅之风,交湘之浦。”《水经注》湘水篇曰:“二妃出入湘之浦。者,水清深也。《湘中记》云:‘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见底石如摴蒲者矢,五色鲜明,是纳湘之名矣。’”据善长说,则湘,犹云清湘。其字读如肃,亦读如萧。自景纯注《中山经》云:“水,今所在未详。”始别湘为二水,俗又改为潇,其谬日甚矣。《诗·郑风》“风雨”,毛云:“暴疾也。”《羽猎赋》“风廉云师,吸〔口鼻〕率”;《二京赋》“飞罕箾”;《思玄赋》“迅猋其媵我”,义皆与毛传同。水之清者多驶,《方言》云:“清,急也。”是则《说文》、毛传二义相因。[4] 这里提供了很多早期“潇”字的例证,无论释为“深清”还是“暴疾”,都是形容词,但是他说郭璞在注《山海经》时已经提出“水,今所在未详”,第一次将“潇”作为水名对待了,此说恐误。查郭注原文为:“此言二女游戏江之渊府,则能鼓三江,令风波之气共相交通,言其灵响之意也。江、湘、沅水皆共会巴陵头,故号为三江之山。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淮南子》曰‘弋钓潇湘’,今所在未详也,潇音消。”[5]可见郭璞并未使用“潇水”一词,所在未详的也不是“潇水”,只是《淮南子》里“弋钓湘”一事罢了[6]。段玉裁不知据何版本立说,徒增疑惑,可置不顾。 那么今之潇水在唐以前是否存在呢?其水当然存在,只是另有专名,也甚混杂。大致说来,由于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两幅地图的发现,我们知道今日潇水及其上游沱水,在汉代称深水,《水经·深水》亦然。从东汉中叶许慎著《说文解字》时起,深水仅指上游,下游与营水合流后改名营水。到《水经注》时期,连上游今之沱水也已并称营水了。详细考证见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7]。 “潇”字为水名,一般公认为最早见于柳宗元的诗文之中,这诚然不错,但一个沿用既久的名称要发生质的变化,当非一朝一夕之功,下文正是要考量“潇”字由形容词转为名词的细致经历及其中蕴涵的缕缕诗意。 “潇湘”在唐前为“形容词+名词”的偏正结构,意与“清湘”同。鲍照《采菱歌》七首之一云:“箫弄澄湘北,菱歌清汉南。”《乐府诗集》注云“一作‘弄弦潇湘北,歌菱清汉南’”[8],“潇”与“澄”可对换,又与“清汉”之“清”对文,其意与清、澄同,明甚!但“潇湘”一词,沿用既久,且其物质指称与“湘”字单独使用殊无二致,于是人们渐渐忽略“潇”字的本义,比如刘长卿《入桂渚次砂牛石穴》诗中有句云:“扁舟傍归路,日暮潇湘深。湘水清见底,楚云淡无心。”[9]诗中“深”、“清”俱另见,“潇”字本义都被抽去了,空空洞洞的一个俗称“潇湘”,与单称“湘”在词义上已没有任何不同,这就为“潇”字与“湘”字剥离,成为单独的名词,准备了心理条件。而“潇”字的独用,开始正是指代“湘”的,杜甫《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中有句:“拨弃潭洲百斛酒,芜没潇岸千株菊。”钱起《省试湘灵鼓瑟》:“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尽管后一个“潇”字《全唐诗》加注“一作湘”,其词义也等于“湘”,但毕竟以“潇”为正文,且不止一例,本文倾向于认为这正体现了“潇”字单独作为名词使用的初期。当然本段所论乃就其内在逻辑而言,不须在引诗时序上一一坐实。 “潇”字真正离开“湘”字及其所指,单独指称另一条水,大约发生在柳宗元贬永州前后,即在公元八九世纪之交,不可能太早。因为诗人元结(719—772)于上元元年(760)起任荆南节度判官,后又代摄节度使事。广德元年(763)与永泰二年(766)两刺道州。道州即在今潇水之侧,若其时潇水之名已著,作为道州刺史的元结不可能一无知晓。但今存元结诗文作品中无一潇水之名,且集内有《阳华岩铭》、《丹崖翁宅铭》、《朝阳岩铭》等,此二岩一崖俱潇水上形胜地,其文无一及“潇”,其《丹崖翁宅铭》反有“零陵泷下三十里”、“丹崖,湘中水石之异者”[10]之类语句,可见他对潇水之名确实不知。 柳宗元(773—819)永贞元年(805)贬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始返,柳子集内潇、湘已明白称二水,如《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诗题即以二水称之。又《愚溪诗序》云:“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分明可见。 吕温(772—811),元和三年(808)贬刺均州,再贬刺道州,五年(810)转衡州刺史。他在道州时,柳宗元正贬在永州,其诗有云:“云去舜祠闭,月明潇水流。”(《道州秋夜南楼即事》)足见潇水之名,确然已立。 贾岛(779—843),生活年代略晚于柳、吕二人,其诗《永福湖和杨郑州》有句云:“嵩少分明对,潇湘阔狭齐。”意为嵩山与少室山相对,潇水与湘水同宽。二水之分,显甚! 从以上三位诗人的诗文例证中可见,至迟到九世纪初,潇水之名已立,与今所指大致相同。不过,在柳宗元诗文中,又常常混淆潇、湘二水,尤其是经常以“湘”称“潇”,比如前引《愚溪诗序》中明明说愚溪(又名冉溪)“东流入于潇水”,则愚溪自在潇水西侧,而其《冉溪》诗则曰“愿卜湘西冉溪地”,此“湘”乃“潇”之误。同样的例句有“遂命仆人过湘江”(《始得西山宴游序》)、“美人隔湘浦”(《初秋夜坐赠吴武陵》),这些“湘”均当作“潇”。由此可见“潇水”之名虽立,毕竟尚未深溉人心,而以湘江总称的传统,尚占相当势力。所以《元和郡县志》中也只有营水,而无潇水之名。 此后潇水之名日渐为人所知,宋以后分别潇湘为二水者渐多,祝穆、朱熹等均有阐述,米芾《潇湘八景图诗总序》云:“潇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湖而南皆二水所经,至湘阴始与沅水之水会,又至洞庭与巴江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潇湘名水;若湖之北,则汉沔汤汤,不得谓之潇湘。”[11]这就将潇湘之名分合的使用情况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二湘与舜妃的传说纠合 屈原《九歌》,哀感顽艳,轻迅昳丽,历来为人激赏,其中咏湘水之神的《湘君》、《湘夫人》篇(下简称“二湘”),尤惝恍凄怨,使人目迷心摇。然而“美要眇”的湘君与“目眇眇”的湘夫人,到底是何样身份,历来颇起争讼,至今未有共识。概而言之有下列数种,因其多为《楚辞》学界习见,为避细琐,仅将各种说法按其出现时代之先后排列,不出引文说明: 1.“湘君”为舜之二妃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刘向《列女传》,此说未及“湘夫人”。 2.“湘夫人”为舜之二妃(或曰三妃)见王逸《楚辞章句》、张华《博物志》。又《礼记·檀弓》中称舜有三妃,郑玄注为即“湘夫人”。此说又不及“湘君”。 3.“湘夫人”为天帝之二女见《山海经·中山经》之郭璞注。顾炎武从之。 4.“湘君”为舜,“湘夫人”为舜之二妃见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此说今人多有信从,游国恩、姜亮夫、文怀沙、马茂元、陈子展诸家均曾伸之。 5.“湘君”为娥皇,“湘夫人”为女英见韩愈《黄陵庙碑》。此说影响亦深,洪兴祖、朱熹、蒋骥、戴震俱从之。 6“二湘”为舜之二女说见宋罗泌《路史·余论九》。 7“湘君”为湘水男神,“湘夫人”为其配偶见王夫之《楚辞通释》。 8“湘君”为洞庭之神,“湘夫人”为青草湖神见王闿运《楚辞释》。 此外,还有一些古代学者以洞庭山神目之,如陈士元《江汉丛谈》、赵翼《陔余丛考》之类,其实山神、水神并无太大差别,即如第六种罗泌之说,也曾以舜帝二女为洞庭山神,但其行迹仍在湘水之中,与“二湘”之辞吻合,不过因《山海经》中有“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之文,故坐实论之而已。各人对“二湘”的身份分配,可散入以上诸说之中,不必俱论。另外,历来好发怪论者也不乏其人,如罗愿《尔雅翼》卷二中以江神奇相为湘君,二女为湘夫人,“二湘”为配偶神云云,即被蒋骥斥为“愚悖甚矣”[12],因奇相本即女性。类似怪论可摒不论。 以上罗列的八种说法,虽未必尽备,但大致涵盖了古代文人对“二湘”身份的主要看法,今之楚辞学者众多,在这个问题上,也大多择一而从、细加论证而已。笔者信从“二湘”乃湘水中原有二女神之说,吟咏者乃男性灵巫,所展演的是人神之恋的欢乐与怅惘,具体论证另文专撰。实际上,笔者这样的立场也只是一种自以为较妥切的选择而已,“二湘”迷离惝恍,诸说也非无容身之地。更重要的是,其凄美的风韵并不因“二湘”身份之不明而稍见逊色。况且,本文的重点也不在乎考定“二湘”的原始意义,而在于考察其作为文学作品被接受的过程,即其意义的生成及再创。我们不妨将上述八种说法稍作归类,一类认为二湘与舜妃有关,计有1、2、4、5四种,二类则与舜妃无关,亦得四种。从时间上看,除第3种郭璞之说外,第二类均起于唐代以后,而在唐以前,将“二湘”与舜妃相关联的观点,是占优势地位的。 当然,“二湘”与舜妃究竟如何关联,也有一个逐渐丰满的过程。早期的说法如《秦始皇本纪》、刘向《列女传》等只说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一笔带过。因何而死?王逸《楚辞章句》注谓二妃“堕于湘水之渚”[13],这一说法逐渐形成共识,以致郭璞注《山海经·中山经》时说:“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后来的重要文献也大多如此。所谓溺死,这里是说二妃无意而失足落水,郭注中就反驳说二妃神通广大,何至落水而不能自救云云。后人可能理会到其中的不吻合处,更可能是要加剧其贞烈的悲剧性,故效屈原故事而创二妃自沉之说。 不止于此,围绕着二妃从征的故事主线,中古之人仍不断地为之添枝加叶,张华《博物志》云:“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14]任昉《述异记》亦云:“昔舜南巡而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恸哭。泪下沾竹,竹文上为之斑斑然。”[15]斑竹本是湘江流域自然生成的一种带斑点的竹子,经此附会,斑竹泣怨,遂成名典。 犹不止于此。二妃故事,深入人心,于是湘水流域便有二妃祠破土而出。最著名的当然是江、湘间的黄陵庙了,早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即记有“湘妃祠”,众注皆谓即指“黄陵庙”,地在湘阴,此时离“二湘”之诞生,尚不足百年。其后,此祠一直存在,时见记载,《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云:“湘水又北经黄陵亭西,右合黄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经二妃庙南,世谓之黄陵庙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潇者,水清深也。”[16]而韩愈《黄陵庙碑》曰:“湘旁有庙曰黄陵,自前古立以祠尧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断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图记》言,汉荆州牧刘表景升之立,题曰:湘夫人碑。今验其文,乃晋太康元年。又题其额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韩愈虽不信舜死南方、二妃溺湘之说,但仍主张“二湘”乃娥皇、女英之神,他在元和十四年(819)贬谪潮州刺史,途经此地时,仍不免“过庙而祷之”。除黄陵庙外,二妃神祀尚有多处,如永州府城在唐代有潇湘庙,道光八年隆庆修《永州府志》卷六《秩祀志》载“潇湘庙”:“旧在潇湘西崖。唐贞元九年三月水至城下,官民祷而有应,至于漕运艰阻,旱干水溢,民辄叩焉。”又湘源县也有二妃庙,柳宗元贬永州司马时,曾作《湘源二妃庙碑》,礼赞有加。 湘妃题材的凄怨诗韵 从前文中我们知道,尽管自唐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二湘”作品与二妃故事相关,但具体如何对应,原是有很大分歧的。但那只是学问家的理性考量,对于诗人来说,他们直披窾窍,分明感受着两者之间在男女、思恋、凄婉、烟水诸方面的相似性,再加上如此深厚的传说背景,因而将“二湘”与二妃长期浸染,混同为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合“二湘”与二妃而创“湘妃”之名。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七《琴曲歌辞·湘妃》记载:“《湘中记》曰:‘舜二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按《琴操》有《湘妃怨》,又有《湘夫人》曲。”[17]《琴操》传为东汉末蔡邕作,今辑本无此二曲,郭茂倩编《琴曲歌辞》,多录古辞,不避伪托。依此体,此不录《琴操》之《湘妃怨》与《湘夫人》二曲辞,或宋时已不可见。《湘中记》有晋人罗含及南朝宋庾仲雍二本,此处未明出何本,要之出唐前之书,则无可疑议。《乐府诗集》之《琴曲歌辞》共收四种湘妃题材的曲子,曰:《湘妃》、《湘妃怨》、《湘妃列女操》、《湘夫人》。又据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18]考索,唐人除琴曲外,琵琶曲中有名《湘妃》者,鼓吹乐大横吹部节鼓二十四曲中有《湘妃怨》。另,教坊中杂言曲子《长相思》,原出琴曲《湘妃怨》,而刘禹锡又创《潇湘神》之曲,等等。可见对湘妃的吟咏,也是唐及唐前文人的一种习尚。让我们来细细品嚼一下这些直接吟咏湘妃故事的歌辞意韵。 唐代以前的作品留存较少,今唯见《乐府诗集》中所存两首《湘夫人》,其一为梁沈约之作:“潇湘风已息,沅澧复安流。杨蛾一舍睇,〔〕娟好且修。捐玦置澧浦,解佩寄中州。”其二为王僧孺作:“桂栋承薜帷,眇眇川之湄。白徒可望,绿芷竟空滋。日暮思公子,衔意嘿无辞。”这二首作品基本演绎“二湘”词句,与二妃事迹几无关联,且情韵清扬而微伤,远不及“二湘”之瑰丽凄怨,足见南朝诗人轻靡而不失温和的诗风。 唐人作品便郁勃慷慨多了,比如郎士元的同题作品云: 蛾眉对湘水,遥哭苍梧间。万乘既已殁,孤舟谁忍还。至今楚山上,犹有泪痕斑。南有涔阳路,渺渺多新愁。昔神降回时,风波江上秋。彩云忽无处,碧水空安流。 此诗显然将二妃事迹与“二湘”情韵溶于一水,且斑竹故事之类后起传说亦已密合无间了。更有李白《远别离》之作专咏舜与二妃事: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冯冯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仓皇叫啸,愁思苦毒,自是李白上承屈原之风,而浓著个性色彩之作。比诸南朝诗风,差之万里,然终是意气之作,难以代表此类作品之风韵。可作代表者,或当推刘禹锡《潇湘神》二曲: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凄怨惝恍,秋水迷离,便是吟咏湘妃一类作品的共同意韵。这种可能源自对早期文学作品的部分误读而形成的一种固定意象及情调(前文交代,笔者认为“二湘”乃吟咏原始湘水二女神,与舜妃之事无关),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中颇为常见,比如《关雎》原非阐述后妃之德,但后人咏后妃之德不妨径用《关雎》,这是继承毛传误读的一种传统;又比如香草美人,在屈原楚辞中容或有所寄托,亦多限于君臣关系,而后人不妨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均借此抒怀。退一步讲,即便湘妃题材并无误读成分,但依循“二湘”的情韵生成,不断实之以传说故事、人文景观,并在同题诗文中反复吟咏,终使这类题材成为典范的凄美意象,则是无可置疑的。 潇湘凄怨情调的唐诗生成 “二湘”凄怨惝恍、秋水迷离的意韵,从一开始就攫住了接受者的心灵,并且在风格上规定着此后二妃传说的衍生及湘妃题材的吟咏,而且,因为在这些故事都发生在湘水流域,因而“二湘”凄怨惝恍、秋水迷离的意韵,也密密地披洒到“湘”或“潇湘”意象中去了。 这在唐以前的作品中已露头角,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王征君》:“窈蔼潇湘空,翠涧淡无滋。寂历百草晦,欻吸鹍鸡悲……北渚有帝子,荡漾不可期。怅然山中暮,怀痾属此诗。”[19]这是直接借用湘妃故事的,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些不涉湘妃故事却饱含“二湘”凄楚风韵的作品,例如: 陆士衡《门有车马客行》:“门有车马客,驾言发故乡。念君久不归,濡迹涉江湘……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20]此写漂泊游子怀乡之情。 张平子《四愁诗》:“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21]此字面写怀恋远人,或另寓深意。 柳恽《江南曲》:“汀洲采白,日落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华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22]乐府江南之曲,常美芳辰丽景,嬉游得时,而柳恽此诗景物故称清丽,仍有故人远方之思,怅惘清婉。此多为唐人效慕。 到了唐代,关于潇湘凄怨的作品,便洋洋大观起来。先引两句初唐概括性的著名诗句: 荆南兮赵北,碣石兮潇湘。澄清规于万里,照离思于千行。(卢照邻《明月引》)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这里“潇湘”与“碣石”相对,作为南北偏远之地的象征,以寄托离愁别绪。而潇湘作为远别离的物化代表,终唐之世其音不绝: 愁思潇湘浦,悲凉云梦田。(刘希夷《巫山怀古》) 北走平生亲,南浦别离津。潇湘一超忽,洞庭多苦辛。(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之问》) 潇湘多别离,风起芙蓉洲。(张泌《湖南曲》) 湘南自古多离怨,莫动哀吟易惨凄。(张泌《晚次湘源县》) 朔漠幽囚兮天长地久,潇湘隔别兮水阔烟深。(杜光庭《怀古今》) 这种凄怨的离愁别绪,固是承续着湘妃遗风,但在唐代一下子涌出那么多潇湘别离的诗文,乃至一提到“潇湘”二字,似乎便会生出一层悄然盈怀、拂之不去的哀愁,又与唐代诗人所处的特定社会生活背景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唐朝是继南北朝数百年战乱分裂后缔建的一个宏大雄健的统一帝国,其政权由北方关陇贵族集团所持掌,它向南方开拓了广袤的疆土,具有强烈的融合南方文化的意愿。当时的北方文化比南方文化发达,官宦、诗人多为北方人士,他们因着各种缘由履迹南方,免不了生出诸种别离的烦恼,这些缘由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贬谪和流放。据李兴盛《中国流人史》总结:“唐代流放地主要是岭南。此外则是今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福建等地。”[23]李书是将贬谪归入流人行列的,所以上述总结实际上是兼指唐代贬谪与流放两种情况。这些流人渡江后,一条主要的线路便是沿着湘江流域南下或北上,著名诗人杜审言、王昌龄、贾至、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韩愈、李涉等均在这条驿路上留下了血泪交织的足迹。 其二,因着江南领土的扩展及其与北方沟通的加深,许多北方诗人也南来为官,著名诗人元结曾二刺道州,张谓曾刺潭州,刘长卿曾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等等。 其三,唐代诗人有漫游天下的习性,李白、杜甫、孟郊、顾况、刘言史等俱曾游历潇湘。 在第一种贬人迁客的笔下,满纸俱是哀愁,如“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柳宗元《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谪居潇湘渚,再见洞庭秋……独攀青枫树,泪洒沧江流”(贾至《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等等,原不足怪。后两种人为何也愁思不减呢?这是因为唐代南方文化毕竟要落后许多,这些为官者、漫游者离乡背井,人事隔膜,也难免临湘北望、惆怅倚之。张谓《同王征君湘中有怀》:“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不用看书帙,偏宜上酒楼。故人京洛满,何日复同游。”其中对京洛的依恋之情,溢于言表!顾况《游子吟》:“……客从洞庭来,婉娈潇湘深……胡为不归欤,泪下沾衣襟……”顾况是苏州人,本属江南,但与潇湘睽隔亦不下千里。故以潇湘来应合游子思乡情绪,殊为允当。 至于带着不如意的心绪来到潇湘者,其下笔成诗,更易流入悲苦之途。孟郊作《下第东南行》:“越风东南清,楚日潇湘明。试逐伯鸾去,还作灵均行。江蓠伴我泣,海月投人惊。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轻。时闻丧侣猿,一叫千愁并。”杜甫晚年漂泊于湖湘之间,并卒于湘水舟中,他去蜀赴湘时,便已意气销磨,生机泯灭了:“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去蜀》) 此外,北人南下还有一种潜在的传统心理,即认为潇湘一带是蛮荒烟瘴之地,刘禹锡《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熊武走蛮落,潇湘来奥鄙”、白居易《得行简书闻欲下峡先以诗寄》“潇湘瘴雾加餐饭”、李咸用《和人湘中作》“湘川湘岸两荒凉”云云。尽管这种印象不一定准确,一些北方人到南方后也能领略潇湘山水的秀丽清雅,但这种传统的心理定势仍然在幽深处隐隐散射,使离别之愁更添苦毒。 因此,在这些南来诗人有关潇湘的作品中,对南北的空间关系便显得特别敏感,“谁当北风至,为尔一开襟”(刘长卿《酬李侍御登岳阳见寄》)、“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韦庄《湘中作》),而潇、湘二水又偏偏都向北流,这分外刺激着南来诗人的抑郁情怀,“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杜审言《渡湘江》)、“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张谓《同王征君湘中有怀》)。 1 e; W% C2 V" I0 d8 K. c
|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