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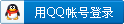
x
几次组合纷纭错杂的“三皇五帝” 刘起釪 一、三皇五帝说的出现 我国的古中传说中,到战国时期才先后出现了好几种以不同人物组合成的“五帝”说;又自战国末出现“三皇”一词,到汉代才开始出现了好几种以不同人物组合成的“三皇”说。而且把后起的三皇排在比它流传得早的五帝前,于是“三皇五帝”就成了我国最早的古史系统。但究竟是哪三个皇?哪五个帝?原是没有定型的。一直到东晋初,在许多三皇五帝说中,才基本定下了一说。由于此一说是由伪《古文尚书》最后确定的,因为“经”重于史,所以此说虽与《史记》所载明显牴牾,也一直为后世所尊奉。但即使如此,晚至萧梁时代,依然还有不同的三皇五帝说提出。 由此可知一两千年来所盛传的为人们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原是纷纭不定,递经战国至汉、晋长时间的不同组合,从神话古史传说众多的古帝先王中,各家各自挑选出三位五位不同人物先后搭凑成好几种不同班底的。 前面《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文中已指出,在西周《诗》、《书》中出现夏、商、周三代祖先宗神禹、契、稷,以及三代开国之君启、汤、周文王、武王,还有姜姓族宗神伯夷、苗族宗神蚩尤、楚族宗神重黎等。至记载截至春秋末期止神话传说的《天问》中,全同于上述古史体系,惟多出了鲧、康回、及商远祖舜,又出现了尧,以及益、羿、少康、王亥、昏微等古帝(神话中帝即神,还有女娲古神)。春秋战国前期的《国语》、《左传》出现了虞夏、商、周四代之远祖神,即多出了虞幕。其他宗神古帝较前亦远为增多,大抵居西边的有出自少典族的黄帝及其后裔十二族之祖与鲧、禹、抒,又帝喾、弃、高圉等。又有出自有氏的炎帝及其后裔伯夷、共工、句龙、四岳等。居东边的有太皞、少昊、颛顼、有穷、高阳、高辛、实沉、阏伯等,自东迁西的有伯翳,自东迁南的有祝融即重黎及其后裔八姓(如季连芈姓,为楚祖),自中迁南的有黎以至三苗,北方有防风氏传汪芒氏、长狄氏,东北有肃慎氏。不详地望的有帝鸿氏、缙云氏、金天氏、烈山氏、陶唐氏(前三者可能在西、后二者可能在东)。战国后期粲然大备的神话全书《山海经》,和《天问》一样没有高阳、高辛、金天、伯翳等,其他《天问》所载及《国语》《左传》所载诸神古帝大抵都有,而多出了数不清的其他神名,如南岳、西王母等,而以帝俊为最煊赫的天神。这一包罗万有的古帝古神全书中惟独没有伏羲,可知华夏族的古帝传说中原无伏羲。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喜称引古帝,但儒墨两家没有提出新的古帝名,只就“二帝三王”宣扬自己的政治学说因而编造出自己的古史说(“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商、周)。《管子》说古帝有七十余家,实只新增了一无怀氏。《庄子·胠箧篇》列举了容成、大庭、伯皇、中央、栗陆、骊畜、轩辕、赫胥、尊卢、祝融、伏羲、神农十二古帝名。《六韬大明》列举十五古帝名,多出黎连、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阴康七名。《逸周书·史记解》列举古帝多达二十六名,则较多为他书所未载。(这里《胠箧》在《庄子》外篇,成书时间晚,采用战国末季秦汉之际自西南民族传来的伏羲氏,他与神农皆列在黄帝后。《史记解》成书时间不详,然更晚,故多异名) 除《六韬》提到有巢外,《韩非子·五蠹》、《庄子·盗跖》也提到有巢。还提到燧人。《荀子·正论》亦言及燧人。而《庄子》的《盗跖篇》以有巢、知生、神农在黄帝前,《缮性篇》以燧人、伏羲、神农也都在黄帝前。 可见古代所传古帝名号是很多的,大都平列地提出,除偶区别时间先后外,并没有区别其高下主次,大家在传说中都是平起平坐一样身分的古帝王。 可是到了战国时代,各国由于斗争的需要,促成了百家争鸣。各家为了宣扬自己匡时救世的主张,都要寻找历史根据,于是历史被纷纷称引,从而出现了一些依托历史旧说加工编造以佐证已说的现象。 当时人所共知的实际历史,是夏、商、周三个王朝,于是“三王”便为战国诸子所经常称引。这是符合客观历史的。但这“三”字也正巧和当时逐渐形成的一个带有某种神秘意义的“三、五”概念相符,人们也正好以确有的三代证实“三、五”概念的有据。结果很多事物都要以“三、五”来称说。如《国语·齐语》:“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韦昭注:“参,三也。伍,五也。”《左传·隐公元年》:“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因举三项,故延及九,然前二者仍是三、五并举。后来的《易·系辞》也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以至一些通常的东西也总是三五相连,如孙武练兵,“三令五申”,见于其本传。国家养老,设立“三老五更”,见于《礼记》的《文王世子》及《乐记》。郑玄《注》说它“取象三辰五星”,“更知三德五事”。处处是三、五并见。至《史记·天官书》承述先秦以来形成的这一概念,为之指出:“为国者必贵三、五。”“为天数者必通三、五”。把“三、五”神秘地推崇得这么具有某种优越意义。既然这么重要,为国者离不开它,治天算者离不开它,普通事物也要用它来套,历史也就必然要用它来套,“三王”一词,就等着有一个什么“五”来配它了。 刚好在春秋时出现了好些霸主,人们看到王业之后继之者为霸业,于是在称述历史时,“三王五霸”一词就自然地出现了。其实在春秋时期先后出现的霸主不止五个,计有:齐桓公、秦穆公、宋襄公、晋文公、晋襄公、晋灵公、楚庄王、楚共王、晋景公、晋厉公、楚康王、楚灵王、晋悼公、晋平公、吴王阖闾、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人,莫不是能主持盟会,号令诸侯,迫使进纳贡献,随同征伐的,他们都是煊赫一时的霸主。按常理,人们据客观事实来称引历时时,有几个霸主说有几个霸主就行了。可是他们偏偏不按历史上实际称霸的人数来说,却硬要按“五”这个数字来称说,把众多的霸主硬说成只有“五霸”,与“三王”一起成为当时称说历史的常语。如《孟子·告子下》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他没有全举五霸人名,只举了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赵岐《注》为它补充了五霸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这是最通行的一个五霸说。由《白虎通》称这是早已流传的一说,可知当是先秦时流传下来的一说。而《荀子·五霸篇》说:“虽在僻陋之国,威震天下,五伯(即霸)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强殆中国。”这是又一五霸说,却是今存战国当时文献中所载之说,是今所见最早的一个五霸说,显然是挑选了春秋时期最强大的五个霸主说的,比上一说中的宋襄、秦穆自然都要强大些。至《白虎通·号篇》引了又一个流传的五霸说:“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阖闾。”这是第三个五霸说,这大概也反映了先秦时的另一说法。到汉代,似乎有人觉得上所举五霸中,有的还不够强大,于是《白虎通》和《风俗通》都主张另一新五霸说,即: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五人。《风俗通·皇霸篇》并说明理由,以为第一说的秦穆、宋襄、楚庄的功业不盛,不足列于五霸,而《国语·郑语》以“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因而定此五霸。这就成了第四个五霸说。这一说不知五霸原是列在三皇之后的,自只能是春秋时代的五霸,引到夏商两代是不合原意的。但由这纷歧的提法中,见出古人被神秘的“三五”框住了,而对客观的历史不去如实地称引它,却硬要从众多霸主中挑出五个来套这“五霸”之数,由于各自的看法不同,所挑选的人就不同,就在“三王”之后出现了好几种任意编排的“五霸”说。 可见“三、五”这一对数字在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中所起的奇特作用。特别是到战国末期,五行说兴起,“五”字更具有特殊意义,自然更要用它来称引事物了。 “三王”的下面配上“五霸”了,“三王”的上面呢?本来在西周之世,人们所知道的历史只是夏、商、周三代,也就是只有“三王”,夏代是三王中最早的一个王朝。可是春秋战国之世,历史知识逐渐扩展,需要向上延伸了。于是就如上文提到的《国语》、《左传》等出现了远古的黄帝、炎帝等古帝,但实际是作为先祖神提出,因帝字的本义是指上帝、宗神。惟在儒墨两家著作中,于夏代前有了人王尧、舜。不过《墨子》的《尚贤中》、《天志》中下、《明鬼下》、《贵义》等篇都只是说“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可见墨子把尧舜列在三代之内,也就是仍在“三王”之内。虽《墨子》书中已有虞在夏前,然其《明鬼下》仍说“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是把虞作为尧舜的时代而仍在三王之内。所以上引《孟子·告子下》也仍只是“三王”、“五霸”连举。但在《孟子·万章》上下中称尧为帝,在《公孙丑上》中称舜为帝,那么在三王之前有了二帝,他所称引的古史,就实际说,已是“二帝三王”的古史了。 这“帝”字的出现,是当时实际政治所要求于古代历史的反映。但标举“二帝三王”,则与孟子之后战国之世所树立起来的“三五以变,错综其数”的原则已不合,必须是“五帝三王”才对。顾颉刚先生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文中说:“战国是一个尽想升级的时代,平民要求高升做官,诸侯也要求高升做王。到宇内有了八九个王时,王位又不够了,就再进一步称帝了。”又在《三皇考》中说:“这件事情虽终战国之世没有做成,可是那时人的心目中,都以为王的上一级是帝,这个观念是已确立了。五帝的系统,《帝典》的文字,就在这帝制运动之下一一出现。”所以这时已不能满足于“二帝”,必须是“五帝”了。于是当时人们开口就是“五帝三王”,如《荀子·大略》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管子·正世篇》也说:“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战国策·秦策》也说:“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又《战国策·齐策》:“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于是“五帝三王五霸”就成为战国后期的学者们所常称说的古史体系了。 直至战国之世终了,古史体系就是这样。一直要到战国结束时期的《吕氏春秋》问世之后,才出现“三皇”一词,那是后话。 二、各种不同组合的五帝说 至于“五帝”究竟是哪五人呢?上引《荀子》、《管子》、《战国策》虽都说到五帝而没有举人名,《孙子·行军篇》说“此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有“四帝”,若加黄帝亦即五帝,然亦未举人名,故梅尧臣校此疑“帝”为“军”之误。惟《荀子·议兵篇》中称尧、舜、禹、汤为四帝。本文前面已引述自西周至战国末所称引的古帝名号那么多,要从其中挑选出“五帝”来,比从十几个霸主中挑选“五霸”困难多了,因而出现的纷歧也更多。但既已确实了只能有“五帝”,各家就不得不从其中挑选出五人来充当此数,于是在古文献中至少出现了六种以上不同的“五帝说”。现依次引述如下: 第一种五帝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明确提出此说者为《大戴礼记·五帝德》,该篇假托宰我问此五帝于孔子,编造孔子答复说: 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帝喾……玄嚣之孙,极之子也,曰高辛。……帝尧,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帝舜,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重华。 这是根据《国语·鲁语》来的。《鲁语》称引了许多古帝,其中有下列赞誉这五人的话: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 《礼记·祭法》也录了这几句,文字略有出入,前两句移到了后面。《五帝德》显然即据此定下这五人为五帝的。《大戴礼记·帝系》并为这五帝编好了以黄帝为始祖的世系,说帝喾和尧都是黄帝子玄嚣一系的裔孙,颛顼和舜都是黄帝子昌意一系的裔孙。而《吕氏春秋·古乐》所叙古帝在禹前者亦此五帝,其《尊师篇》亦同。后来《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五帝即此五人。这是我国古代最初的一个五帝说,时在战国后期。 第二种五帝说——庖牺、神农、黄帝、尧、舜。 持此说者为《战国策·赵策》及时代更晚的《易·系辞》。按《系辞下》云: 古者庖牺[1]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战国策·赵策》在汉代经刘向整理编定时,文字受了后来影响。其文云: 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机。 是明以此五帝置于三王之前。《庄子·缮性》亦历叙伏牺、神农、黄帝、唐、虞为天下,但在伏牺前多了一个燧人。《淮南子·俶真篇》历叙伏羲、神农、黄帝,《汉书·律历志》录《三统历》,亦叙自伏戏至黄帝、尧、舜,中略神农未提,然可知皆承此一五帝说。《资治通鉴外纪》反对三皇五帝说,但其所列最早的帝王即此五人。总之此一五帝说影响自颇深远。 顾颉刚先生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2]一文中对此二个五帝说有很好的论析。该文《〈世经〉以前的古史系统》一节中说:“在许多古史系统中,只有黄帝、尧、舜是不缺席的。再有二人,就很难定。一派说这二人是颛顼、帝喾,别一派则说是伏羲、神农。说颛顼、帝喾的,以黄帝为五帝的首一帝,与驺衍时的史说合,可以称为‘前期五帝说’。说伏羲、神农的,以伏羲为首一帝,黄帝居五帝之中,殆是秦以后的史说,可以称为‘后期五帝说’。这两种学说各有其畛域,不容相混。……黄帝是最早的帝王,兼为颛顼和帝喾的祖父,又为‘百家言’的中心人物,其势力之大自不消说。尧、舜靠了‘天下之显学’儒墨二家的鼓吹……舜又是田齐的祖先,齐人是最夸诞的,他们的势力也正不可一世。在这种环境之下,五帝的座位哪能不请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去坐,哪里再有空位给与炎帝。所以炎帝虽和黄帝同时出生(《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而竟致落伍了。到了秦汉,许多小民族已团结为一大民族,颛顼、帝喾也失去了人们的需要。那时道家极盛,他们笃信‘世代愈古则人民愈康乐’的历史律,要找黄帝以上的帝王来压倒黄帝以下的帝王……而伏羲、神农在黄帝前的系统遂得确立。又因为有了他们的鼓吹,而儒家也把这两位古帝请进了《易》的范围。可是‘五帝’是只许容纳五个人的,挤进了伏羲、神农,只得挤出了颛顼、帝喾,因为他们的地位已经不重要了,有类于战国以后的炎帝了。” 这是对这两种五帝说形成的最好的说明。但另又出现了第三种五帝说,而顾先生未加论列,由于此一五帝说曾把五帝送到天上之故。 第三种五帝说——太昊[3]、炎帝、黄帝、少昊、颛顼。 这是把以前未被拉入的炎帝和被挤出的颛顼重新请来,和黄帝一起,同东方古史传说中有名的太昊、少昊两帝搭配成一个新的“五帝”班子。这显然是战国之末奠定、至汉代形成和确立的“阴阳五行说”所创。持此说者,始见于阴阳五行说的原始经典《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其文云: 孟春之月……其帝太暤,其神勾芒。 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季夏之月……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孟秋之月……其帝少蓐,其神蓐收。 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这是把已成人间帝王的这五人配为五时(四时加季夏)的帝,又使之神化。高诱注则以为原是人间的五帝,死后祀为此五方之帝。《礼记·月令》全袭用了此说,录其全文。《淮南子·时则篇》亦全承此说,则以为此五帝分司着五方。而《淮南子·天文篇》则又以为是五星之帝,太皞、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分别配木、火、土、金、水五星。《淮南子》这两篇是高度发展的汉代阴阳五行说的主要经典,因而把这五帝完全五行化,使之和五行说中一切五的东西相配。但到王符《潜夫论》中,明确表示不相信当时已有的“三皇说”,只相信五经所载,因而据《易·系辞》有伏羲,确定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轩辕、少皞挚、颛顼高阳为人间历史上的五帝。不过据当时纬书说他们是由神明感生,才兴起而有国家的。而且还把古史传说中的各古帝及其族属都分别划归这五帝的血胤系统,说只有这五帝世系的后代才可以轮流受天命为帝王。这是五德终始说下帝系的进一步编造,是古代各五帝说中特异的一说,大旨已见本书《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第八节。 第四种五帝说——少昊、颛顼、喾、尧、翼。 这是根据西汉末出现的《世纪》[4]按五德终始说依五行相生次序所排定的一个古帝王系统表来的,由伪《古文尚书·序》确定此五人为五帝。《世纪》所排定的古帝王系统前面八位是: 太昊炮牺氏——(共工)——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率氏——(帝挚)——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 这是按照木火土金水相生顺序排列的,其中共工、帝挚不在五德之内,故不计入。这一系统的前面五个,全同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所列,在黄帝与颛顼之间有一少昊。而汉代自《尚书大传》以下好几种纬书都把伏羲、神农列为三皇。于是在当时通行的五帝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人之间多出了一个少昊,五帝成了六人。郑玄在《中候·注》中解释说:“德协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5]如果他此说能成立,五帝有六人,就成为另一种新的五帝说了。但其说本为王肃所反对,孔颖达又详驳之,故其说未成一说,且五帝而有六人,亦不合通常事理。故不认郑玄此注为一说。至伪《古文尚书·序》云: 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孔颖达《尚书正义》释之云: 坟,大也。以所论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故孔君以黄帝上数为皇,少昊为五帝之首耳。 从此《世经》所编排的古帝系统,前面三帝就定为三皇,接着的五位就定为五帝。黄帝本来称之为帝,且明明是五帝之首,为了解决少昊列为五帝的问题,就硬把黄帝这第一个帝升为三皇了。其实这是东汉纬书《礼纬·稽命徵》以来已有之说,硬把黄帝升为三皇。至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亦照此列为三皇,把少昊以下五人列为五帝。伪《孔传》实亦阴承此诸说。由于“经”重于史,此说明明与《史记》所载第一五帝说相冲突,亦为人所尊信。《旧唐书·玄宗本纪》记天宝六载,“于京师置三皇五帝庙,以时享祭”。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六“三皇五帝”条云:“唐天宝中祀三皇则伏牺、神农、黄帝,祀五帝则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盖用颖达之说。”[6]可见此说已列为国家功令。因之历代史籍大都承此说,直至清代吴乘权《纲鉴易知录》向民间广泛传布历史知识,亦用此说。这一说就基本成为我国晋以后所共尊的三皇五帝说,奉之为古代信史了。 第五种五帝说——喾、尧、舜、禹、汤。 这是一度定为国家典制,但终于很快即被废弃的一说。顾颉刚先生在《三皇考》[7]中考定王莽依董仲舒的“三统说”,把本代和前二代列为“三王”(即本届的三统),三王之前的五代列为“五帝”,五帝前的一代列为“九皇”。不过改董氏“九皇”一人为“三皇”三人。《汉书·王莽传》记王莽夺得帝位后,分封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禹、殷、周、汉之后,以奉祀他们。顾先生在排比王莽给这些帝王的后代所封情况后说:“同时应封伯者三,封侯者五,封公者三,恰合三皇、五帝、三王的次序。……从此可知王莽的‘三皇’是黄帝,少昊,颛顼;他的‘五帝’是帝喾,尧,舜,夏,殷;他的‘三王’是周,汉,新。” 原来王莽用董仲舒三统说稍加改易,实际把自战国以来形成的认识古史的模式,即“三皇、五帝、三王”之说,用来套从自己王朝向上溯的历史。于是按他的新代所定的历史,“五帝”就是喾、尧、舜、禹、汤了。只是由于他的王朝短命,所定的“三皇”“五帝”很快即被废弃。如果他的王朝历史久远,它的学术文化对后代影响大的话,则他定的这一五帝说必将也是很有影响的一说。 第六种五帝说——黄帝、少昊、颛顼、喾、尧。 持此说者,是晚至南朝萧梁时的梁武帝。《资治通鉴外纪》引录其说云: 梁武帝以伏牺、神农、燧人为三皇,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帝尧为五帝,而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与三王为四代而已”[8]。 前于《外纪》的孔颖达《尚书序·正义》已引此,但语颇缺略,但批驳了此说。其文云: 梁主云《书》起轩辕,同以燧人为皇。其五帝自黄帝至尧而止。知帝不可以过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与三王为四代而已。”其言与《诗》之为体,不《雅》则《风》,除皇以下,不王则帝,何有非王非帝,以为何人乎?《典》《谟》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按梁武帝萧衍当时以好儒学称,且有著述。《梁书·武帝本纪》称萧衍“少而笃学,洞达儒玄。……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这样一部600卷的大书,当是他敕令臣下编篡的,他只是亲自写了赞和序。而这样一种创新的说法,大概臣下不敢妄撰,应该出于他自己的意见。不过他也有所本,本文前面引述《墨子》屡次将虞和夏商周合在一起,启发他作此说。看来其意是要把黄帝保留在五帝之内,而少昊被人称引已久,又不能去掉,故为此委曲之说。这大概是历代编造五帝说的最后一说了。以上共达六种五帝说,如加上郑玄说,则更有七种五帝说。 此外还有天上的五帝说。 由于帝字的本义是指上帝、宗神,它原是存在于神话中的。殷代卜辞中的帝即指上帝,但到殷末几位商王为抬高和神化自己,便称起帝乙、帝辛了。不过人们知道他们是自比上帝,帝字的本义仍没有变。所以周代文献中仍以帝指天神,一些神话专著如《天问》、《山海经》中凡称帝某的,无一不指天神。特别是作为神话百科全书的《山海经》中那么多帝某、帝某,从他们的活动看,无一不是神,虽然有些后来进入普通文献中历史化了,人化了。但它在《山海经》中的本义全都是神,所以古代神话中叫做“帝某”的神,是很不少的。 由上文已知道,到战国后期已习用“五”来称呼事物,所以在群神众帝中,也有了“五帝”的称呼。如采缀战国儒墨等家遗文撰成之《晏子春秋》,有“景公欲使楚巫请致五帝以明君德”为题的一章,述使楚巫致五帝之事。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云:“五帝,五方之帝。”又如《楚辞·惜诵》有云: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令五帝以中兮,戒六神与向服。 王逸注:“五帝,谓五方神也。” 是即五方之帝。由于五方配了五色,所以也就是以五色为名之帝。如《史记·封禅书》云: 秦中……唯雍四畤上帝为尊。 《索隐》:“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后宣公作密畤,祠青帝;灵公作上畤,祠黄帝,作下畤,祠炎(赤)帝;献公作畦畤,祠白帝。” 《史记·封禅书》下文续云: 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这就使天上五方帝青、黄、赤、白、黑五帝的祀典齐全。其时天上的星座也有五帝,如《甘石星经》说: 天皇大帝一星,在钩陈口中。又有五帝内座五星,在华盖下[9]。 《史记·天官书》都予以记录,前者在中宫紫宫,称“太一帝居”;后者在南宫太微宫,称:“其内五星,五帝坐。”发展到东汉纬书,给天上这些五帝都起了名字。如《春秋纬·文耀钩》云: 太微宫有五帝座星。苍帝春起受制,其名灵威仰;赤帝夏起受制,其名赤熛怒;白帝秋起受制,其名白招拒;黑帝冬起受制,其名汁光纪;黄帝季夏六月起受制;其名含枢纽[10]。 这是指太微宫内五星五帝坐。但是纬书在当时是各逞异说的,也有像《淮南子·天文篇》那样指木、火、土、金、水五星的。此说见《河图纬》云: 东方青帝灵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黄帝含枢纽,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汁光纪,水帝也[11]。 顾颉刚先生在《三皇考》中指出:“那时的信仰是天人合一的,看人间的五帝即是天上的五帝。”这话完全不错,上引第三种五帝说的太皞、炎帝、黄帝、少昊、颛顼本来说成是人间的五帝,可是却又是天上五方五星的五帝。上文引高诱注,还只是解释为,原是人间的五帝,死后上祀为五方之帝。可是纬书却不如此解释,故《三皇考》继续说:“纬书的作者是把天神和人王的界限打通了的。他们觉得人间的五帝和天上的五帝(太微宫五星)是一非二;降则在地,神即人也;陟则在天,人即神也。”于是各种纬书进一步创造了许多感生说。如《孝经纬·钩命决》云:“华胥履迹,怪生皇牺(伏羲)。”《春秋纬·元命苞》云:“有神龙首感之于当羊,生神农。”《诗纬·含神雾》云:“大电……感附宝而生黄帝。”《春秋纬·元命苞》又云:“女节梦接,意感而生白帝朱宣(贾逵谓即少昊)。”《诗纬·含神雾》又云:“摇光……感女枢,生颛顼。”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中全承了这些感生说。至郑玄注《礼记·大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一句,亦全用感生说,其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感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他把上面引述各神灵感生,改为全由太微五帝之精感生,即伏牺由灵威仰感生,神农由赤熛怒感生,黄帝由含枢纽感生,少昊由白招拒感生,颛顼由汁光纪感生。这就看出天上五帝对人间五帝关系之大了。所以要用隆重的祭礼去祭。 王肃是专反对郑玄的。郑玄这样的怪说他自然极力反对。《礼记·祭法篇·正义》引录王肃之说,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为:“谓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颛顼配黄帝而祭。”顾先生《三皇考》据此指出:“他(王肃)主张人间的五帝都是黄帝的子孙,不是太微五帝之精所生。”王肃对郑玄的批驳可说是正确的。但古帝本出于神话,把它人化而编成历史人物,本来就捉襟见肘,随时露出神话破绽。现在再回到神话里增加一些涂饰,本来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差,要知人间五帝也好,天上五帝也好,全都是些妄诞悠谬之说,都是不可信的。 三、各种不同组合的三皇说 人间历史上的“五帝说”已盛行后,直至战国末季,还没有出现人间历史上的“三皇说”。可是天神的三皇说在战国末季却出现了。而到战国结束时期写出的《吕氏春秋》一书中,开始出现人间历史上的“三皇”一词,但没有具体的人名。可知这显然是受神秘的“三、五”这套数字的概念影响下,率意地顺口说成的,所以举不出人名。也有不可免的因素是,人们好古,喜欢层累地向上追加古史,在已习惯于五帝说之后,又要向上追溯,以致三皇说终于不免产生出来了。 顾颉刚先生曾撰有一篇十五万多字的长文《三皇考》[12],由杨向奎先生协助写成,通过极详尽、深入的研究,完善地解决了三皇的问题。此处大体上利用了该文成果,作了些补充,扼要地引述各次出现的三皇说,而不能涉及顾先生文中许多重要的考订。顾先生文中共论述了四种不同的三皇说,那是主要的四说,本文则就文献中所提到的,共搜列六种不同的三皇说。 本来“皇”字在早先的文献以及金文中,只是形容词或副词,为尊大、美善之意,常用以形容上天、上帝和祖先。到战国中后期,把神话中帝尧帝舜等作为人间帝王来称呼,而战国群雄中的强者也争想称帝,天帝位号归了人王。于是人们开始把常用以形容天帝的皇字移作天帝的位号,因而《楚辞》的《离骚》里有了“西皇”,又以“皇”字直称天帝,《九歌》里有了“东皇”、“上皇”,《橘颂》里有了“后皇”,皇成了上帝的称谓,以前叫“帝”、“上帝”或“后帝”的,此时叫“皇”、“上皇”或“后皇”了。 当时把皇的名位看做比帝高,如《管子·兵法》云:“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庄子·在宥》也说:“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这是又把皇字称人王后的说法,但实际当是“帝”已称人间帝王之后而“皇”尚称天帝时,认为上皇高于人帝所形成的概念。于是在战国末盛称“三、五”的风习下,既然有了“五帝”,在其上面自然就是“三皇”了。 很显然,最初的三皇是指天神,与五帝初为五方帝之称天神并无二致。最早见于文献的,是在秦完成统一六国的时期里撰成的《吕氏春秋》。在该书的《贵公篇》里说: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这显然可理解为天神的“三皇五帝”。可是该书下面三处却不同了: 《用众》: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禁塞》: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 《孝行览》: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 这显然指人间的帝王了。此外,成书时代较晚的《庄子·天运篇》也说: 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仪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仪法度…… 余语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
' k" i" ^- v' Q9 a; G+ T8 o
: X/ t1 S8 r( \( A7 U9 o( R @ |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