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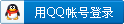
x
在历史与理想之间:对《史记》中 尧舜禹时期政治形态的解读 刘明涛 高民政 《史记》中尧、舜、禹时期政治形态的实质 “尧、舜、禹的时代是我国原始公社社会就要没落,私有财产社会就要建立的时代。”[1]这段时期,中国原始氏族社会逐渐解体,并向奴隶社会转型,还没有产生文字,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太明朗的章节,但这个时代是“一个社会生产力比以前大发达的时代,进步较速,由量变达到质变的时代”[2],存在着较发达的政治现象。在《史记》的记载中,尧、舜、禹时期的政治建设已具备一定规模。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闪现着“民主”思想的火花和以民为本的政治思维,也构建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政治运行机制,有一套“准制度化”的政治习惯作保障,并有一定的政治机构设置。比如:政治的轮换与交替实行“禅让制”、原始的民主决策机制、权力的分工协作等等。从某种角度讲,《史记》中记载的这一时期已经有了国家的雏形。这些描述与一般史学家们的看法相去较远,到底如何认识和评价《史记》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 史家对历史的记载和论述都是建立在大量文献的收集、整理之上的,或多或少地渗透着自己的一些理解,反映着阶级的意愿和当时的社会认识。二千多年前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是一样,他为尧、舜、禹作传,不可能绝对地秉执春秋之笔,毫无主观意愿地书写历史。从资料准备看,经过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次政治因素对学术的沉重打击之后,司马迁所掌握的资料应比早他500多年的孔子时代更为缺乏。而从资料来源看,司马迁所依据的资料很大部分都是儒家经典或经儒家思想加工过的传说。司马迁自己承认,“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3]在《史记》之前,对尧、舜、禹时期有所记述的典籍有《尚书》前三篇:《尧典》、《皋陶谟》和《禹贡》,《大戴礼记》两篇:《五帝德》和《帝系姓》,这都是儒家的经典。第三,从《史记》成书的时代背景来看,司马迁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司马迁受到儒家的影响很大,其思想中有很深的儒家烙印。从司马迁的自传中我们可以印证这一点:司马迁虽然对诸家均有针砭和评述,但显然对儒家的肯定较多,特别是对儒家的经典论著大加赞赏[4]。这段历史的不明朗性与《史记》成书的背景相对比,凸现出有关记载的“儒化”色彩。由此看来,《史记》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政治形态的描述其实质可能具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历史的幻象,二是儒家民本政治理想的折射和具象化,而且,构建民本政治理想模式的意义更大于描述原始民主政治的意义。 实践与体系:折射着儒家民本理想的政治建构 儒家通过对尧、舜、禹这段历史的记载、加工,渗入其民本政治的思想,初步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政治、社会模式,并通过司马迁之笔在《史记》中展现了出来。透过《史记》中有关记载,我们可以对这种理想中的政治形态进行素描,大体勾勒出一个轮廓。 一、民本政治思想的体现 1.重民利民的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民本政治的核心理念,着重体现为重民利民的思想。但重民利民、以民为本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只是社会精英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思考问题,谋划政治,这一点在《史记》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中体现比较充分。比如,尧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有所犹豫——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还是禅位于舜?最终“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5]。尧公私分明,大公无私,将帝位禅让给德行、能力出众的舜,完美地体现了儒家关于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符合儒家“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最高政治伦理,所以大受后世推崇。再比如:大禹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6]。还有,皋陶和禹在舜前论政时,其围绕的核心之一也是如何安民,如何为民谋福祉,如何得到民众的拥护,等等[7]。不管这些例子是史实,还是儒家的附会,从中可以看到儒家寄托的政治理想。 2.德法并治的思想。《史记》中这段历史的记载,不仅充分地反映了儒家德治仁政的思想,而且也反映出了一些法治思想。其“法治”思想既包括制度化的层面,也包括以“刑”威服。“制度”层面上的“法治”后将论之,此处单就以“刑”服人凡举一二例。比如:在尧舜时期有“四凶”害人,“天下恶之”,“尧未能去”,“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8];再比如,皋陶、舜和禹辩论之后,“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9]。这是明显的威服之举。还有,舜确定皋陶职责时说:“汝作士,五弄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10]可见,这种政治形态不是一味地提倡仁政德治,而是德法并治,王霸之道并举,但总体讲是“德治为体,法治为用”的模式。 二、民本政治的权力运作 1.最高权力的承继(领导人的选定程序)。从《史记》的记载中分析,在尧、舜、禹时期,领导者的交替非常理性、慎重,体现了民本政治试图通过禅让制弥补“人治”弊端的设计。其基本程序如下:通过民主推荐,初步确定帝位候选人,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考查,对其品行和能力进行全面的考核和鉴定,拟定为帝位继承人,使其摄政锻炼并进一步考察。当上一代君王逝世,天下守孝3年后,将政权还于“法定”继承人(上代君王的亲子,习惯上的继承人),之后根据民意所向确定真正的下一代君王。《史记》记载,尧在选择继承人时问四岳:“‘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11]由是众人推荐了舜。“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帝位。”[12]其间,舜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查。在舜五十八岁时,尧逝世,天下大孝三年后,舜还政于尧的儿子丹朱,但是“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13],于是舜践天子位。舜禅位给禹时,禹也是众人推荐,并经过了重重考验,舜丧三年后“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但“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14]。禹禅位给益也基本遵循了这个程序,但益没有得到天下人的认同而失去了帝位。由此可以看出,“部落酋长的儿子具有做酋长继承人的优先权”15,但这种优先权是与选贤用能、民意决定的原则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一种“竞选”。 2.政治权力的分工。《史记》记载的尧、舜、禹时期,政治权力划分已经比较明细,既有集中与分工,也有协作与平衡。(1)天子(首领)与四岳。在这一时期,天子是“具有超凡魅力的圣王,拥有相当大的权力”[16],同时存在着“议行合一”的机构——四岳,翦伯赞先生认为它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关,也即部落酋长会议”[17]。四岳与天子分享着权力,并为天子提供建议,帮助决策,甚至驳回天子的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子个人的能力、品行与威望。(2)地方与中央。《史记》中记载舜“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18],这十二牧有可能是由部落首领转化而来的地方官员;另外,“夏后之制,亦置六卿,其官次第,犹承虞制”[19]。在舜主政时,平行地设立了一些职能部门,并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比如:任命禹为司空:后稷主农业;契任司徒,负责民政:皋陶主管刑罚:由垂负责手工业;伯夷主礼仪:夔负责文教等等。[20]从这些痕迹可以推测这一时期可能已经有了中央与地方划分的雏型,而且中央权力在天子(首领)之下又有了明确的分工,这是一个政权逐步完善的显著象征。(3)舆论监督。舆论在当时也发挥着强大作用。如在舜时代,“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21]。这使得下情得以上达,有一定的检查、监督和反馈功能,部分地使政权成为一个闭合得较科学的整体。这种监督覆盖了所有的权力主体,也包括最高统治者天子(首领)。《吕氏春秋·自知》曰:“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22]这表达了最高权力主体通过舆论的监督进行自我约束的意愿。与现代民主政治相比较,这种民本政治模式有“议行合一”和“协商”的特点,而且也设有司法和监督部门。但其监督部门的地位和作用似乎比司法部门更超然,而且是一种柔性的监督,只能借最高权力者的道德素养发挥作用,是一种典型的人治体系。 三、民本政治的“制度”建设 在尧、舜、禹时期,还没有成文的制度规范,但分析《史记》中的记载,其时存在着习惯性的规则或“准制度”,且大多与“禅让制”相配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度的保障作用。为行文方便,以制度论之。 1.民主决策制度。其政治权力运行基本上按照议政的方式实施。重大的政务均由“四岳”集体商讨,由大家提出意见作出对策,而得到天子或众人的认可后,再加以落实。如,尧选择继承人时征求众人意见:“谁可顺此事?”放齐推荐尧的儿子丹朱,兜推荐共工,因丹朱“顽凶”,“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均被尧否决。最后尧要求“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人将身处民间、贤能而又以孝闻名的舜推荐给尧,并得到了尧的认可。另外,在决策时天子(首领)充分尊重其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如:尧征求治水人选时,众人都推荐鲧。尧认为其能力不足以担此重任,但岳提出异议,认为“异哉,试不可用而已”,由于岳的坚持,“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23]。由此可见,这种决策方式不是下级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其中体现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也充分尊重少数派、尊重下级的意见和建议。 2.考行考功制度。为保证领导者的品行和能力,要对其进行一系列的考查。舜被确定为继承人人选后,接受了广泛、严格、长期的考察: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舜相处,以观其外。考察后发现,舜对女色非常节制,为人处事十分得体。而且舜也具有极强的凝聚力,所居住的地方,“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也具有过人的胆略和知识,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深入深山大泽之中仍不迷路。通过这一系列考察,尧才决定将帝位禅让给舜。考行考功制度还伴随着竞争。根据《史记》记载分析,舜在选择继承人时,“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24]辩论为政之道,实行公开竞争,然后根据皋陶、禹的品行修养、能力和功劳大小决定帝位归属。严格的考行考功制度也针对其他官员。如舜时代任命二十二个人分管不同的工作,规定每三年一考功,根据连续三次的考核成绩决定提升或罢黜。因为有这个制度保障,所以“远近众功咸兴”,“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25]。 3.培养“试用”制度。尧、舜、禹时期对帝位继承人都有很长的培养“试用期”。如在舜30岁左右时,尧发现舜并开始培养,长达20多年。舜50岁时代尧摄政,开始试用阶段,直到61岁时才正式登基,其试用期也长达11年。禹在接受舜的禅位之前,有13年时间在外治理水患,并任司空等重要的职位,接受了充足的培养煅练,舜将禹定为继承人之后17年后辞世,加上大孝3年,禹的“试用期”长达20年。禹禅位给益的情况也基本相同。所以注重培养继承人并对其进行较长时间的试用是选拔贤明的领导人的重要措施。 4.让辟制度(民意决定)。舜、禹在正式继位前都将权力归还给“法定”的继承人,如舜将帝位还于尧的儿子丹朱,禹将帝位还于舜的儿子商均。由人民在指定继承人与法定继承人之间选择,得到人民拥护者正式践行君王之职。禹将君位传给益,在禹辞世后,益也按这个习惯将帝位还给禹的儿子启,辟居于箕山,由人心所向决定天下归属。但因益的威望不足,天下终以启为君。可以这么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最终的领导者是由广大民众选择和决定的,是民意决定的,因此也具有最大的合法性。 破灭与追求:为什么儒家的民本政治可望不可及 《史记》中尧、舜、禹时期的政治形态实质是儒家民本政治的理想模式。虽然儒家政治思想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终究没有实现这一理想。其中,有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但从这种政治设计本身探究,也有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儒家的民本政治淡化或回避了个人的利益追求。儒家民本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本或民本观念强调的是‘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平等;民主观念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来导出人格平等”[26]。这一点可以从尧、舜、禹时期原始政治与古希腊雅典城邦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对比中凸显出来。因为对人性、权利和利益的不同认识和追求,希腊城邦奴隶制民主用比较极端的抽签方法决定执政官、将军等职务,并制定严格、完备的法律来保障执行,力求机会均等,而儒家几千年一直渴望“圣王”的出现,并设想依靠道德的力量约束社会精英的行为,促使其勤政爱民,力求保障并实现国泰民安的社会。儒家在民本政治理想的建构中,不仅回避人民政治上的诉求,而且有意无意地打压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其理论上的动因走向了偏激。追溯这种现象,有两个可能的理论起点:要么儒家将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看得高于一切,其他的(特别是个人利益)都微不足道,甚至忽略;要么儒家从根本上反对对利益(政治的和经济的)的追求,从而塑造一个静态和谐的、只讲人性不讲利益的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和利益的分析方法来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放弃个人和阶级利益,也绝不容许其他个人或阶级侵犯他们的根本利益,但却利用儒家的这种思想禁锢民众,愚弄人民放弃自己的权利,满足于最低的需求。当社会的主体失去了对自我合理利益追求的理由之后,整个社会也缺乏前进的动力。儒家的民本政治理想就如一辆没有汽油的汽车,就算车况良好,没有什么故障,也是开不动的。 其二,儒家的民本政治是不完全的,小范围的“民主”。儒家的民本政治实质是建立在对“民”的二重性理解的基础上的。在民本政治思想中,“民”首先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百姓、平民甚至奴隶都是“民”,他们的整体意志得到充分的重视,“作为一个整体,民的地位和价值有可能高于君主”[27]。于是,便有了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理论上,政治的一切归宿也落实到他们利益的保障与实现上。“一旦把‘民’或‘庶人’具体为个人,或者说民众的整体价值体现于每一个体的时候,民也将相应地变得至微至贱”,他们只是被统御的生灵,“每一个具体的‘民’,只是整体的民的一个分子,他只不过分享了整体的价值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无贵可言了”[28]。所以,从本质上说“民”只“是一个剥夺了每个个体的整体”[29]。这种对“民”二重性的理解既重视人又忽视人,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民本政治中权力(利)享受的不均衡性。民本政治只是从经济(民生)角度认识整体的“民”,忽略了个体的“民”的政治权利,而这些政治的权力(利)只集中在受到良好教育的上层社会手中。被推崇的理想社会——尧、舜、禹时期——也是一样。一方面,尧、舜、禹都有“皇”族血统,从其谱系看都是黄帝的后裔。所谓的民主选择有一定的范围(这可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但终究带有儒家思想的印迹);另一方面,民主(即选举权)也有一定范围,是贵族、诸侯或部落首领的民主。至于政治上的其他权利就更不用说了。虽然儒家在不断的追求中逐步地改良这种体制,在权力的两端开辟了一个通道,将士(文人)通过考核的方式也纳入到统御者的方阵,使社会的下层通过自我努力也能挤入上层社会,有分享个人权力与权利的机会,但终究没有突破对“民”二重性理解的藩篱,民本不可能转化为全方位的民主。这是儒家民本政治理想始终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 其三,儒家的民本政治是人治体系。民本政治内含着森严的等级性,而且从体制建设上讲是不完善的,或是和其人治体系相配合的。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0]。因此,整个民本体系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讲求“礼、德”治国,整个政治的生态决定于领导人的品行,没有根本法作保障。幻想天子皇帝都是圣人贤人,有高洁的道德品质,内圣而外王,和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异曲同工。但儒家的民本政治又是实质上的世袭制(由于权力与利益因素作用,政权交替时“世袭制”很容易战胜“禅让制”)、终身制,这与其“圣王”追求产生了根本的对立。“因为父是圣人,子不必便是圣人。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世世代代的圣人在事理上是办不到的;因而在位者便不必有德,而有德者也就不必在位。”[31]一旦在继位者选择上出现偏差或无法选择出合格的人选时,整个政治生态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本政治用“禅让制”来进行理论上的弥补,但在人治体系下,君权高于一切,没有一个根本法保障这种制度的实施,会有几个君王能做到这一点?反倒是,“与君主专制思想、等级观念糅合在一起的民本思想没有撼动甚至是加固了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32]。由此看来,民本思想虽然对“君本”思想及其制度具有牵制和约束作用,但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君本”政治框架下的自我防范机制。在以民本为掩护的“君本”体制下,法律建设如同儿戏,就算是建构起来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也是空中楼阁,注定不会长久。启得天下之后,这种政治形态逐渐解体,“家天下”的思想确立,也印证了这一点。 其四,儒家民本政治的“减压阀”的弹性太大。换一句话表述,也即保证这种政治体系的条件太宽泛。所谓政治“减压阀”是指,政权需要从政治层面上进行改革,从而释放、缓解或消除因社会问题积累到某一程度而形成的压力状态。政治“减压阀”与政治生态和政治发展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减压阀的弹性太大,社会、政治在短期内是稳定的,中期是波动的、反复的,社会在反复挫折中小步发展前进;减压阀弹性太小,社会政治在短期内极易起波澜,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只能取一个合理的阀值范幽,政治减压阀才能够起到调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政治的长期稳定的作用,同时,通过改革和改良逐步解决出现的问题,促进社会在中长期内以较高的速度发展、进步。 “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之于政治的最终理想就是天下太平。”[33]这反映了儒家民本政治的减压阀的上限——天下安定,民众安居乐业:其下限是社会严重动荡,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种弹性极大的阀值幅度使社会、政治失去应有的生气和活力,使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它很难为社会进步积蓄强劲的动力,而且容易走向两个逻辑上的极端。第一个极端:只看重国泰民安的上限。当政治体制发生某种质的变化时,人们只考虑在短期内是不是冲撞了这一标准,而不从长远考虑这种变化的利与弊,所以放任这种变化,最终可能在麻痹中失去了这种制度。尧、舜、禹时期原始政治的解体正是在这个情况下悄然进行的。第二个极端:只以减压阀的下限规范政治活动,无视人民生活的每况愈下,听任社会矛盾的积累,在政治人物普遍认识到要改善人民生活之前,社会矛盾已经到了极其尖锐、不可调和的地步,人们也因为无法继续生活和生存,被迫拿起武器,以暴力的手段进行反抗,以争取自己的利益。儒家民本政治的“减压阀”标准很长时间一直被继承着,并在政治生活中有所体现。但历史总是和儒家开着玩笑,几千年来,按儒家政治思想治理的中国,始终不是在渐进的变革中稳步前进,这与民本政治的减压阀设置或许有一定的关系。 参考文献: [1][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5~26页。 [3][4][5][6][7][8][9][10][11][12][13][14][18][20][21][23][24][25]司马迁:《史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0、3352~3354、14、31、53~55、17、57、17、11、19、14、58、17、17、17、11、53、17页。 [15]许树安:《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19]袁刚:《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7]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22]徐子宏等译:《白话吕氏春秋》,岳麓书社,1996年,第627页。 [26]邵汉明:《中国文化精神》,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1页。 [27][28]孙晓春:《儒家民本思想发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5期。 (《史海钩沉》2005年第11期) 1 y* [0 G8 k0 e+ S/ d
|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