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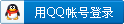
x
湘君湘夫人简论 黄士吉 《湘君》、《湘夫人》人们通常叫“二湘”,是《九歌》中最动人、最令人喜爱的篇章,也是《九歌》中情节最完整、最富悲剧色彩的作品。我国战国时代产生了如此完美感人的歌舞剧文学作品,这是很了不起的,它纠正了过去中国戏曲史研究的某些错误论断。但是楚人祭祀中的湘君和湘夫人所指的究竟是哪个神灵,“二湘”表演的到底是什么内容的神话故事?前贤的研究成果已很可观,但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七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二湘”表演的是湘水神追求洞庭神的恋爱故事。 水出于山,水神住在山上,比如《九歌》中的河伯就在昆仑山上(即黄河发源的地方)。湘夫人(即湘水神)住在九嶷山上;洞庭湖中则有君山,湘君应住在君山上。湘水可以赴君山,事实上也是湘江水流入洞庭湖,而洞庭水却无法泛上湘江,所以传说中则想象为湘水女神往赴湘君,湘君则无法来就湘夫人,这确实是既合地理又富人情的优美的想象。 第二种说法认为“二湘”表演的是关于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当然这并不排斥第一种说法。因为洞庭水神可以说是舜,而湘水神可以说是舜妃)。湘君是男神,湘夫人是女神。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认为“帝子降兮北渚”中的“帝子”,是“言尧二女,娥皇、女英,随舜不及,堕湘水中,因为湘夫人”(转引自唐代李善注《文选·西京赋》“感河冯,怀湘娥”句,梁·萧统《文选》卷二,第47页)。显然,王逸认为湘夫人为女神,即娥皇、女英。而湘君为男神,可以说就是舜。 第三种说法认为“二湘”表演的是帝舜三妃登比氏与娥皇、女英之间的矛盾(详见本文《湘君》今译中关于“下女”的注释)。 第四种说法认为“二湘”表演的是娥皇、女英的故事,即“二湘”为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湘君是娥皇,湘夫人是女英。主张此说的有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朱熹在“帝子降兮北渚”中注云“帝子,谓湘夫人,尧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韩子(韩愈,引者注)以为‘娥皇正妃’,故称君;女英自宜降称夫人也”;“君不行兮夷犹”句,朱熹注云“君,谓湘君,尧之长女娥皇,为舜之正妃者也”。 第五种说法认为“二湘”是舜的两个女儿宵明、烛光,也有说宵明、烛光是娥皇的孪生女儿。 第六种说法认为“二湘”为《列仙传》中的“汉妃”二女,处江为神,既不是舜二妃,也不是舜的女儿。 第七种说法认为二湘是配偶神,与二妃无关。顾炎武认为:“湘君湘夫人,亦谓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江湘之有夫人,犹河雒之有宓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安得谓之尧女?且既谓之尧女,安得复总云湘君哉?”(《日知录》卷二十五)顾炎武排弃旧说,而把“二湘”看作为原始时代初民对自然的崇拜,认为二妃之说是后人加上去的传说。 上述诸说,各言其是。我们认为,只有根据“二湘”作品内容本身来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才是最可靠的。《湘君》中明明有“吹参差兮谁思”句,《湘夫人》中有“九疑缤兮并迎”句,即可证明。关于“参差”,蒋骥注云:“洞箫,舜所作,其形参差不齐,象凤翼也。”洪兴祖《楚辞补注》云:“《风俗通》云:舜作箫,其形参差,象凤翼参差不齐貌。”“九疑缤”,当是指九嶷山一带大小神祇,这就与关于舜葬“九疑”的传说和记载相符合。显然,那种认为“二湘”与舜的传说无关的各家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二湘”既然是远古的爱情故事传说,那么说是舜的两个女儿也不甚妥当。那种认为湘君为娥皇、湘夫人为女英的看法,恐怕与“二湘”内容也不符合,而且真的如此,那便是《湘君》写娥皇的哀怨,《湘夫人》写女英的悲哀,那么“二湘”内容岂不重复了吗?因此,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认为“二湘”表演的是关于舜与二妃的爱情故事传说,较符合原作内容。这个远古时期的传说是很动人的,现存有关这个传说的资料是比较丰富的。 舜,“号曰重华”。《楚辞·天问》云:“舜闵在家,夫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文中的“姚”,即舜姓。意思是说舜忧闷地待在家中,父亲为何让他独身?帝尧嫁女不通知舜家,娥皇、女英怎可(与舜)成亲[1]?王逸注云:此“言舜为布衣,忧闵其家。其父顽母嚚,不为娶妇,乃至于鳏也”,“尧不告舜父母而妻之,如令告之,则不听,尧女当何所亲附乎”。看来,舜与娥皇、女英的婚姻在一开始就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关于尧“以二女妻舜”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载: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 《史记》的这段记载似对《天问》提出的尧嫁二女于舜的问题作了回答,显然尧嫁二女给舜,是有着通过女儿考察继承人舜的明显政治目的的。后来舜接受了尧的禅让,做了部落联盟领袖。但有的研究者说,舜接受尧的禅让,做了部落联盟领袖,“并娶了尧的两个女儿为妻”,从文字上看,似乎舜娶尧二女为妻是在舜接受禅让之时或之后,这与《史记》的记载是不符合的,不知何据。 《史记·五帝本纪》又云:“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九疑山,隔湘江,跨苍梧野,连营道县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九疑山。”九疑即九嶷山,在湖南宁远县南六十里。《郡国志》云:“九嶷山有九峰……四曰娥皇峰,峰下有舜池……六曰女英峰,舜葬于此峰下……”南朝人任昉的《述异记》说:“舜南巡不返,殁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恸哭,泪下沾竹,竹上文为之斑斑然。”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云:“斑竹即吴地称湘妃竹者,其斑如泪痕……世传二妃将沉湘水,望苍梧而泣,洒泪成斑。”“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李白《远别离》中这两句诗便是写二妃追舜不及,泪染湘竹之事的。而屈原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根据神话传说成功地塑造湘君、湘夫人艺术形象的伟大作家。 舜妃,即湘夫人。刘向《列女传》云:“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娥皇为后,女英为妃。”但乍看起来,“二湘”中的舜妃(湘夫人)似无两人(娥皇、女英),因此历来研究者或译者往往把湘夫人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来处理,这显然跟舜与二妃的爱情故事不相符合。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解释说,这是屈原根据舜与二妃的传说加工改写的,可不必受传说的约束。但无论怎样加工改写,都不应离开故事本身改写后二妃成了一个“湘夫人”,这是不合情理的,显然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在翻译“二湘”时,也遇到了“湘夫人”是否二妃的问题,一时未能解决。后来在译“二湘”结尾时又遇到了“捐玦遗佩”、“捐袂遗褋”的问题,我因此对传统的解释更产生了怀疑:湘夫人为何捐玦后,紧接着又弃佩,湘君为何在捐袂后,又接着遗褋呢?后来我将这个问题与湘夫人是否二妃、“二湘”是否写的是舜与二妃的悲剧故事这个问题联系起来研究,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朱季海在《楚辞解故》中说“湘君、湘夫人之文,于此初无二致,惟以‘玦佩’、‘袂褋’为异耳”,朱先生没有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究竟“玦佩”与“袂褋”是怎么回事呢? 洪兴祖《楚辞补注》云:“玦、佩,贵之也;袂、褋,亲之也。”可见,“玦佩”与“袂褋”的用处是不同的。玦、佩当是玉玦、玉佩之类珍贵的装饰品,湘君将玉玦、玉佩分别赠给了娥皇、女英。《湘君》中的娥皇将湘君赠的纪念物“玦”、女英将湘君赠的“佩”,相继遗弃,娥皇将玦抛进大江,女英将佩扔进澧水,以此见其思怨之极。那么《湘夫人》中的“袂褋”又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关于“玦佩”,各家解释出入不大的话,那么对“袂褋”则众说纷纭。 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将“袂”译为“套袖”,宫九奇《屈原诗歌新译》亦从郭说。文怀沙《屈原九歌今绎》将此句译为“把我的衣袖抛到江心”。古代女子是否有套袖?而“衣袖”又怎能抛到江心?陆侃如等注的《楚辞选》则云“‘袂’或当作袟,是传写的错误。袟是小囊,妇女所佩”,似有道理,但不知有何根据。至于“褋”,陆侃如等则注云:“褋或当读做褋,指环的古名。”如果“褋”是古环,那岂不与《湘君》中的“玦佩”无异了吗?湘君与湘夫人将一个古环赠来赠去,如同“投我以木瓜”,对方又以“木瓜”回报,这怎么可能呢? 王逸《楚辞章句》注云:“袂,衣袖也”;“褋,襜襦也。屈原设托与湘夫人共邻而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将适九夷也。”王逸说是屈原在捐袂遗褋,后来有人说捐袂遗褋的是湘夫人,又有说捐袂遗褋的是舜,但无论是屈原,还是湘夫人或舜都不可能“捐弃衣物,裸体而行”,即使在古代,恐怕这也是不成体统的。此说虽然可笑,但王逸却告诉我们,袂不可捐而褋不可遗,否则就会裸身而行的,即袂褋当是衣物。而袂褋是谁的衣物呢? 洪兴祖《楚辞补注》说:“袂、褋,亲之也。”因此,我们认为“袂”,本意为衣袖。长袖善舞,衣袖在这里借代为女子衣物。褋,可解释为汗衫、单衫之类,较为妥当。《湘夫人》中的“袂褋”都可以说是女子所用衣物,以之赠给湘君(舜),以示亲近之情。用自己身穿的衣服送给心上人,这在古代女子的爱情生活中是常见的。《左传》曾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戏于朝。”袒服,是贴身穿的衣服。可见,湘夫人将自己穿的衣服赠给舜,是完全可能的。但令人难解的是,湘夫人赠给湘君一件“袂”,还感到不足以表达其亲近之情,又接着赠给湘君一件“褋”,似无这种可能性。据此,可以断定当是娥皇赠给湘君“袂”、女英赠给湘君“褋”,湘夫人当是娥皇、女英二妃。《湘夫人》中的湘君是在望之不见、近似绝望时将娥皇赠给自己的信物“袂”和女英的“褋”,相继遗弃湖畔,这种解释可以说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 由此可见,通过“二湘”内容本身来研究湘夫人是否二妃的问题,是最可靠的方法。不只“捐玦遗佩”、“捐袂遗褋”,还有《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句,似也能证明湘夫人是娥皇、女英二妃。 《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句,我们认为这是用白芷、兰草两种香花芳草象征娥皇、女英的。但蒋骥其注云:“沅则有芷,澧则有兰。言神之无定在也。”即说女神时而在沅,时而在澧。蒋注说对了一半,即沅芷、澧兰是“言神”的,即指的是湘水女神,但说女神飘忽不定,这种解释恐与下句“思公子兮未敢言”似难衔接,女神飘忽不定与思公子未敢言不知在内容上有什么必然联系。王逸《楚辞章句》则注云:“言沅水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以兴湘夫人美好,亦异于众人也。”王注认为这里以芷、兰兴娥皇、女英二妃的美好超群,接着写二妃思念湘君(公子)之切,蕴藏在内心的深情不敢倾吐的心理。作者在这里赋予楚地植物以艺术生命,使全篇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更重要的是以白芷兰草的芳香美丽来比拟、象征娥皇、女英二妃的芳洁。此句诗似也透露出湘夫人是二妃,而非一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屈原的“二湘”表演的内容是以远古时期帝舜与二妃的爱情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湘夫人”指的是娥皇、女英二妃。 所谓“湘夫人”,意即“湘(君)的那个人”,犹今之妇女称自己丈夫为“我那个人”一样。“夫人”,是一般的指示代词,当那个人、那些人或众人讲。如《左传》襄八年“夫人愁痛”,其注云“夫人,犹人人也”,“释文”:夫音扶;《左传》昭三十一年:“所能见夫人者,有如河!”注云:“夫人,谓季孙也。”这里的夫人,当那个人讲。“夫人”成为贵妇人的专称,本是儒家适应贵族统治的需要而对这个古词汇作的曲解。但湘夫人是湘水女神,又是舜妃,尊为夫人,是当之无愧的。只是这样称呼,失去了原意“湘君的那个人”那种亲昵之情罢了。 “湘夫人”是勤劳善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女性。据有关资料记载,帝舜南巡,没有带二妃一起去,后来娥皇、女英追踪而至,到了洞庭湖滨,听到舜死苍梧的噩耗,悲痛欲绝、泪如泉涌,“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李白的《远别离》就是写的这个内容。娥皇、女英寻夫无着,自投湘水,殉情而死。这引起了当时人们普遍的哀悼和纪念,当地人民把她们埋葬起来,并把她们当作湘水女神,立祠祭祀。应该说,“二湘”真实地反映了人民悲欢离合的现实遭遇和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 但是封建统治者则与人民的愿望恰恰相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衡山:《括地志》云:“在衡州湘潭县西四十一里)。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音者)其山”(按:湘山祠:《括地志》云:“黄陵庙在岳州湘阴县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祠。二妃冢在湘阴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庙在山南,故言湘山祠”)。 《史记》的这段记载表明,至少自秦以来人们便已经将娥皇、女英作为湘水女神来纪念了。传说中的舜是一个爱人民的君王,而娥皇、女英也是谦虚勤俭的女子,决不因自己是帝尧的女儿就骄盈傲慢的。人们立祠纪念,正说明人民对帝舜和二妃的深切怀念。而秦始皇在神祠避风浪,一怒之下竟命刑徒将古祠烧毁,只能证明其为十足的暴君罢了。 然而人民心目中的湘夫人形象是任何封建统治者抹杀不了的。战国时期伟大文学家屈原塑造的湘君、湘夫人形象,尤其是感人至深的湘夫人艺术形象将永远留在人间。“二湘”把娥皇、女英与帝舜那种生死契阔、会合无缘的苦衷表现得那样一往情深,生动地反映了二妃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虽然思怨无极,却总是锲而不舍,充沛地显示出一种生命的活力,高度地概括了人民真诚淳朴、坚贞不渝的高尚情操。 湘神本是楚国境内所专有的最大河流湘水的化身。这一神祇最初也和天上云神日神一样,是初民崇拜自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从自然背景上看,湘沅二水源远流长,丰饶秀丽,她们宛如一对“要眇宜修”而又生死与共的姊妹,二水又都流入洞庭湖,这样人民便把它和帝舜与二妃的远古神话传说结合起来,从而使原来抽象的神的概念逐渐凝成具体的形象,并设想神也和人一样有爱情的生活,这样神的形象更丰富,与人民现实生活更接近了。楚人“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祭祀歌舞当然用以娱神,娱神同时也往往是娱人。因此,《九歌》内容大都糅杂着许多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二湘”所表现的也是神的儿女之情。这样,祭祀神祇便往往成了青年男女发展爱情的好机会。 同《山鬼》一样,那种从生活深处发散出来的哀怨幽思,使“二湘”笼罩着一层忧伤郁抑的悲剧气氛。很难看出,它“可能是屈原年轻得意时的作品”[2]。而“二湘”所抽绎出来的那种坚贞高洁、缠绵哀怨之思,应该是屈原长期放逐中现实心情的自然流露,其寓意是深刻的,这和屈原的其他篇章表现的思想也是一脉相通的。 “二湘”的突出艺术成就就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湘君、湘夫人的艺术形象,而在艺术手法上,更有其独到之处。 《湘君》中的湘君,楚人祭祀时可能由男巫来扮,而由主祭女巫迎神;《湘夫人》中的湘夫人则由女巫来扮,由主祭男巫迎神,互相酬答,边歌边舞。祭祀时当有男女众巫助祭,而参加祭祀的也随之或歌或舞。《湘君》主要用湘夫人的语气写成;《湘夫人》则主要用湘君的口气写的。《湘君》表现湘夫人追寻湘君时那种期之不来、怨慕悲伤的心情;《湘夫人》则表现湘君思念湘夫人那种望而不见、会而无因的苦闷。《湘君》与《湘夫人》是姊妹篇,两篇都以候人不来为线索,着重写企待对方来而产生的深切思慕之情。两篇都写那坚贞不渝的爱情,写那会合无缘的悲哀,又都没有作正面描写,而是通过对方心理活动的深刻刻画来塑造湘君和湘夫人形象的。这样,写思念对方,既写了对方,更同时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写一人同时写了两人,这就收到了一石双鸟、用笔简洁而又相映生辉、情味隽永的艺术效果。我们用温庭筠《菩萨蛮》“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这句词,来说明“二湘”的艺术手法,可以说是比较贴切的。 “二湘”虽都侧重在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也有比较完整的戏剧情节,而在情节发展的“紧要处”则“重著精神,极力发挥”。如《湘夫人》自“筑室兮水中”到“建芳馨兮庑门”一段竟长达十四句,这是湘君痴立洞庭湖畔沉浸在幻想中的唱词。黄昏时,他仿佛听见娥皇、女英二妃的召唤。于是,他冥想着自己一旦和二妃重新团聚时应该在水中建立起一座什么样的房子。这本来是空中楼阁,是蜃楼海市,可是屈原却将这镜花水月、虚无飘渺的东西写得那么具体逼真,连续用许多芳草香花,絮絮叨叨,读来却不感到重叠繁复,而更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此刻湘君对二妃的深切思念之情。但在收场时却不见湘妃降临,这种转喜为悲出其不意的转折造成了强烈的节奏,增强了戏剧效果,也更使全剧增添了浓厚的悲剧气氛。 “二湘”在语言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它的优美不在于刻意求工,精雕细刻,而是单纯自然,有如一股清清的泉水。同时,“二湘”的语言又是准确精炼的。剧中人物语言因人物身份、性格和地位的不同而有区别,这使人物语言带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比如《湘君》结局的“捐玦遗褋”,使我们由此断定主祭者当是扮演娥皇、女英二妃的女巫;《湘夫人》结局的“捐袂遗褋”,为我们断定主祭者当是扮演湘君(舜)的男巫,提供了线索。 “二湘”不仅通过剧中人物的语言可以确定人物的身份,更可以看出其不同的性格特征。 《湘君》结局时有“时不可兮再得”的唱词,深刻揭示了湘妃那欢情不再、会合无缘的悲哀心理;《湘夫人》结局时有“时不可兮骤得”的唱词,此句与前篇的“再得”恰成对照。洪庆善《楚辞补注》云:“不可再得,则已矣。不可骤得,犹冀其一遇焉。”洪庆善说得对,看来《湘夫人》中的帝舜并未因湘夫人未来而就此绝望,是说与湘妃团聚的时机不可以仓促得到,他并没有因暂时挫折而灰心丧气,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他要比湘妃坚强些,这种对比突出了帝舜的性格特征,同时这个悬念也给读者以轻微的慰藉。一字之差,却准确地表现出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 “二湘”语言凝炼,很富于表现力。如《湘夫人》帝舜的登场唱词“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便是有名的例子。仅此四句,屈原就扼要地把故事发生的时间、环境、人物的思想感情、人物之间的关系等,通过湘君帝舜的口作了说明。后世戏曲的“自报家门”、“定场诗”,可能滥觞于此。在湘君的想象中,湘夫人是在那一片波光水影、风声雨意中姗姗而降的。开端这满纸的风波,满眼的落叶,满怀的秋思,满天的离愁,使全剧弥漫着浓烈的悲剧色彩,开场的这四句唱词也为全剧的悲剧结局定下了基调。这里的深秋景物秋风、木叶、湖水,组成了萧瑟悲凉、富有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它又与主人公舜的内心情绪是那样协调,从而给人以强烈的感染。作者在这里没有直接写此时湘君的心情,而是通过在湘君面前展现的深秋景色,通过湘君想象中的湘夫人形象,生动显示出湘君那惆怅忧伤的情怀,这恐怕就是湘君的登场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的原因。娥皇、女英驭风飞临的形象使湘君彷徨怅惘,更感染和启迪了古往今来的许多诗人。情中有景,景中有人,情景交融这个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在我国可以说是有其渊源的。歌德在《歌德对话录》(朱光潜译)中说:“他们(指中国文学——引者注)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一切景语皆情语”,我们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这句话来说明“二湘”中的景物描写,也可以说并非过誉之辞。 当然,正是洞庭、沅湘水那烟波微茫、竹林幽翳的自然景象,反映在屈原的作品中,才使屈原的“二湘”充满了浓郁的沅湘之间的地方色彩,从而也加强了“二湘”的悲剧气氛的。屈原把人民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感情糅合在一起,从而使这一悲剧故事又交织着炽热而缠绵的情调。这种炽热追求的绵长细流,宛如涓涓细水在幽涧里低回,使歌舞剧“二湘”的内容更丰富,尤其使湘夫人的艺术形象更丰满动人,形成了“二湘”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而扩大、加深了远古优美神话传说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时至今天,“二湘”仍然继续给人以强烈的美的享受。 注释: [1]闻一多《楚辞补注》谓:“闵乃妻之误,夫乃父之误。”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亦从闻说。本文仍从旧说。 [2]郭沫若《屈原赋今译》。 (《鞍山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 j" @( \/ k, p; M+ D | 
 /1
/1 